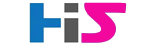我们来聊聊德国品牌“阿德勒”(Adler)。
“阿德勒”(Adler)这个名字在德语中意为“鹰”,这个名字确实非常贴切地描绘了该品牌曾经的光辉与象征意义。然而,正如你所说,这只“飞鹰”如今已不再翱翔于德国工业的蓝天。
以下是关于阿德勒品牌的一些关键信息:
1. "辉煌历史":
"起家于自行车":阿德勒品牌起源于1886年,最初在德国埃森(Essen)生产自行车。它在早期就非常成功,是德国自行车制造业的领先者之一。
"转型汽车工业":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阿德勒在1898年推出了其第一辆汽车。这使其成为德国最早生产汽车的厂家之一。
"航空业的先驱":阿德勒在航空领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德国最早制造飞机的厂家之一(早在1909年就生产了首架飞机),还曾是世界知名的飞机制造商。阿德勒飞机以其高质量和可靠性而闻名,不仅用于竞赛,也大量用于军事(如侦察机)和民用(如邮政、旅游)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阿德勒航空都是欧洲领先的飞机制造商之一。
"多元化发展":除了汽车和航空,阿德勒还涉足过摩托车、雪橇等交通工具的制造
相关阅读延伸:德国品牌“阿德勒”:一只逝去的飞鹰
德国品牌系列之(阿德勒)
故事的主人公叫海因里希·克莱尔(Heinrich Kleyer)。这哥们不是什么天生的猛男也不是什么世代贵族,他爹是个机械工头,家庭背景顶多算是个技术工人。克莱尔这小子从小耳朵里听的不是莫扎特而是齿轮咬合的吱嘎声和蒸汽锤砸铁的咣咣声。在这种环境里泡大的克莱尔对机器有种近乎变态的痴迷。书本上的知识满足不了他了,二十岁来岁的时候他就揣着几个马克像个要饭的似的一路跑遍了半个欧洲。汉堡、维也纳、巴黎、伦敦,哪儿的工厂最新潮,哪儿的机器最牛逼他就跟蚊子见了血一样扑上去。那会儿的德国看英美就像今天某些人看硅谷一样,恨不得把人家的脑子挖出来安自己脖子上。克莱尔在英国第一次看见一个有着巨大前轮外带一个小得可怜的后轮,人骑在上面摇摇晃晃像马戏团小丑的东西叫“便士-法寻”(Penny-farthing)就是最早的自行车。克莱尔这小子看到这玩意儿就感觉是发现了一座金矿,二话没说回到国内就在法兰克福古滕洛伊特街95号租了个小破车间挂上了“Heinrich Kleyer & Co.”的牌子,开始倒腾起了这玩意儿。但干起来克莱尔才发现这英国原装的自行车太他妈贵了,一个普通德国工人不吃不喝干一年都买不起。怎么办?那就拆,然后仿!克莱尔把英国人的设计图纸当成《九阴真经》那样认真研究。他发现英国人的设计有很多华而不实的地方纯粹是为了贵族老爷们看着爽。于是,他把那些没用的装饰全给砍了,用更结实,更便宜的材料替代,造出来的车样子丑是丑了点,但结实耐操,价格还直接腰斩。1886年,他给自己的产品起了个名字——“Adler”,阿德勒在德语里是“鹰”的意思。不过,这鹰一开始就是个土鳖。但架不住这土鳖便宜,实用,就这样一下卖疯了。法兰克福的邮差开始骑着它送信,小老板们骑着它去收账,连妞儿们都开始穿着大长裙歪歪扭扭地学着骑。而克莱尔的小作坊也在几年之内跟滚雪球一样变成了法兰克福最大的工厂之一。有钱了,人就容易飘。但克莱尔却不是!他好奇心重,总想着找更有挑战,更新奇的玩意儿玩。接着他又开始满世界溜达。这次,他看上了两个新东西:一个是打字机。当时打字机已经出现,以美国雷明顿公司(没错,就是那个做枪的)的打字机最为著名。但这打字机笨得像个小棺材,而且设计结构和盲打没啥区别,打一行字你得把整个机架掀起来才能看见自己都打了些什么鬼。克劳斯觉得这特么就是侮辱智商。他从美国挖来一个叫惠灵顿·帕克·基德(Wellington Parker Kidder)的工程师,俩人关在小黑屋里天天叮叮当当地敲,1898年,他们敲出来了阿德勒7型打字机。这款打字机在当时简直就是个黑科技。它革命性地采用了“前击式”结构,你打的每一个字母都清清楚楚地印在眼前。这让那些抄抄写写的文员们效率提高了好几倍。阿德勒打字机就像今天的iPhone重新定义了一个行业。由此,克莱尔的商业帝国也就又多了一条粗壮的大腿。另一个,就是那冒着黑烟,发出拖拉机般噪音的汽车。19世纪末,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已经让四个轮子的怪物在德国的土路上跑了起来。但那玩意儿与其说是车不如说就是个移动的锅炉!又贵又容易散架。克莱尔也是好奇就买了一辆法国德迪翁-布东(De Dion-Bouton)公司生产的小车。那车的设计就是个装了发动机的敞篷沙发,乘客和司机面对面坐着,专业术语叫“Vis-à-Vis”,屁股底下是一单缸发动机,突突突地跟抽羊角风似的,一路跑一路还满是汽油味。克莱尔开着这破玩意儿在法兰克福街头转悠,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马被惊得当街大小便失禁,贵妇们吓得花容失色。但克莱尔在那一刻听到的不是噪音而是未来的交响乐,他知道这玩意儿将来一定会取代马车成为普罗大众的交通工具。他没犹豫,直接跟德迪翁-布东公司买了发动机的生产许可,而且连壳子都懒得设计直接把法国人的拿过来换上自己更结实的底盘和轮子贴上“Adler”的鹰标,直接开卖。这就是阿德勒的第一款汽车,“Adler 4.5 PS Vis-à-Vis”。克莱尔的逻辑简单粗暴:老子既然能让全德国人都骑上自行车就能让他们都开上汽车。他把造自行车的思路运用到了汽车上:结实可靠,其他都是扯淡,别整那些没用的。早期的阿德勒汽车没什么驾驶乐趣也没什么豪华内饰,就是个能把你从A点移动到B点的工具。但它不容易坏!在那个汽车比婴儿还娇贵的年代,“不容易坏”就是最好的卖点。就这样,靠着自行车和打字机赚来的真金白银,克莱尔把阿德勒这只鹰一脚踹上了天。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这只鹰将来会飞得有多高又会摔得有多惨。他只是个痴迷于齿轮和活塞的老派德国商人用一生的固执给这只鹰造了一副钢筋铁骨,一副能跟别人死磕的铁骨。克莱尔这人抠。抠到什么程度?他能为了一个齿轮的成本跟工程师吵得唾沫星子喷对方一脸。但他又极度大方,只要他认定一个人很牛逼就敢把自家的金库钥匙直接扔过去。1902年,他就这么扔了一次。他找到了一个叫埃德蒙·伦普勒(Edmund Rumpler)的奥地利人。这哥们儿,你都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他。这他妈就是个从达芬奇手稿里爬出来的魔鬼。他脑子里装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机械图纸,在来阿德勒之前就已经折腾过蒸汽机、内燃机甚至还给戴姆勒公司画过设计图。但他脾气臭得跟谁都尿不到一个壶里。他觉得别人都是傻x,而别人也都觉得他是个不切实际的二货。克莱尔却不管这些,他从埃德蒙·伦普勒的图纸里看到了这哥们儿脑袋里有座别人看不到的火山。他把伦普勒请到法兰克福给了他一个独立的部门,撂下一句话:“钱,我给;人,你挑。给我造个全新的从里到外,每个螺丝钉都刻着‘阿德勒’名字的汽车。别特么再让我看见法国人设计的影子。”伦普勒没让他失望,把自己锁在车间里带着一群被他骂得狗血淋头的德国技工开始了一场革命。1903年,他们先是拿出了一个怪物:阿德勒的第一台自研四缸发动机,还发动机和变速箱整合成了一个单元。这在今天听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可是开天辟地。当时的车发动机是发动机,变速箱是变速箱,中间靠着一根又长又不可靠的链条或者皮带连着。跑在路上,链条断了,皮带松了是家常便饭。你得停下来满手油污地去伺候这祖宗。而伦普勒直接把这两东西铸造在了一个壳体里,用齿轮直接咬合。这一下就把汽车的可靠性提高了一个等次。这个被称为“一体化动力单元”(unit construction)的设计让阿德勒汽车瞬间跟所有竞争对手拉开了代差。当别人还在路边修链条的时候,阿德勒的车早已一溜烟跑的没影了。克莱尔看着这个设计,据说半天没说话,最后就憋出俩字:“妈的,真是特么的天才。”有了独门绝技,下一步干嘛?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是傻X才干的事。真爷们就是直接上战场,把对手的头按在地上摩擦,而那个年代汽车的战场就是赛车。那时候的赛车不是今天这种在光滑赛道上跑圈,那纯粹是玩命。没有柏油路全是土路、石子路。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成百上千公里。车手旁边必须坐个机械师,因为车随时会散架,爆胎,断轴,发动机起火。赢了,你就是英雄,你的车就是神车;输了,或死,或残,或根本没人记得。克莱尔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个比赛:“赫科默挑战赛”(Herkomer-Konkurrenz)和“亨利亲王杯”(Prinz-Heinrich-Fahrt)。这是当时德国乃至欧洲最严酷的汽车拉力赛,是检验车辆性能的终极考场。他把两个儿子埃尔文(Erwin)和奥托(Otto)直接推上了驾驶座。这老头子够狠,别人的爹都是怕儿子出事,他是亲手把儿子送上绞肉机,就为了给自家产品做个活广告。画面切到1908年的亨利亲王杯。埃尔文·克莱尔开着阿德勒赛车,车身窄得像个棺材,四个轮子细得跟自行车胎似的,脸上糊着防风镜,嘴里全是土。旁边坐着机械师,怀里抱着备用零件和工具,俩人颠得昏天暗地。赛道是乡间土路,路边挤满了看热闹的农民。突然,前面一辆奔驰赛车过弯太快,一个轮子直接飞了出去,车子像陀螺一样翻滚着冲进路边的沟里,当场起火。而埃尔文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一脚油门踩到底从旁边呼啸而过,溅起的泥点子打在了旁边燃烧的残骸上。这不是冷血,这是那个时代赛车手的生存法则,但凡犹豫一秒钟,后面的人就会把你撞飞。阿德勒的车就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打出了名声。当那些设计更激进、马力更大的意大利车、法国车,纷纷在半路抛锚、自燃、散架的时候,那只黑色的鹰总能满身泥泞但姿态优雅地冲过终点线。连续几年,阿德勒在这些大赛里都名列前茅,虽然没拿到太多冠军,但“可靠”这个标签像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在了德国人的心里。“开不坏的阿德勒”,成了当时一句响亮的口号。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阿德勒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业巨兽。它的厂区大得像个小城市,烟囱林立,一万多名工人在里面像蚂蚁一样的忙碌。产品从自行车、摩托车到各种型号的汽车再到打字机火的一塌糊涂。它的旗舰车型比如“Favorit”和“Trumpf”(王牌),已经成了德国中产阶级家庭身份的象征。海因里希·克莱尔这个从修车铺里走出来的老头,此刻已年逾花甲。他站在自己的办公室窗前,看着自己庞大的工厂帝国,那只鹰的标志在法兰克福上空闪闪发光。他成功了,他把一个被人嘲笑的铁架子变成了德意志的骄傲。这只鹰羽翼丰满,爪牙锋利正准备翱翔于整个欧洲之巅。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看到的只是风暴来临前最后一次平静的日落。天边已经泛起了血色,不是晚霞而是战争的颜色。一场要把整个欧洲都拖进绞肉机的战争正在悄悄拉开序幕。1914年8月,萨拉热窝一声枪响,战争来了。海因里希·克莱尔的办公室里不再是讨论下一代发动机的设计图而是一张张来自柏林总参谋部的军用订单。上面没有“请”和“谢谢”的礼帽用语,只有型号、数量和最后期限。德意志的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国内所有的工业齿轮都必须以同一个节奏、同一个方向疯狂地转动,任何异响都会被碾得粉碎。阿德勒,这只黑色的雄鹰一夜之间从一个骄傲的工业制造商,变成了一个毫无感情的军火承包商。工厂的节奏也全变了。生产“Favorit”轿车的生产线被拆得七零八落,取而代之的是粗犷,笨重的卡车底盘。那些曾经用来打磨镀铬装饰件的灵巧双手,现在开始给军用摩托车边斗装机枪支架。车间里弥漫的不再是机油和皮革的混合香味,而是浓烈的硝烟,铁锈和死亡的味道。伦普勒,这个魔鬼工程师,他的天才大脑也被征用了。他不再为那0.1秒的圈速提升而绞尽脑汁,而要计算一辆满载炮弹的卡车如何在被炮弹炸得像月球表面一样的佛兰德斯泥地里不至于陷入泥潭。他设计的那些坚固可靠的“一体化动力单元”,现在成了把一车车年轻生命精准运到凡尔登这个“绞肉机”里的高效工具。克莱尔的那两个赛车手儿子埃尔文和奥托也脱下了赛车服换上了灰绿色的军官制服,不再在阿尔卑斯的山路上玩漂移,而是在西线的弹坑间驾驶着阿德勒生产的指挥车躲避着随时从天而降的榴弹。他们曾经为“亨利亲王杯”的荣誉而战,现在是为了德皇的野心而战,或者说是为了活下去。阿德勒还生产了大量的军用救护车。白色的车身上印着红十字,也印着那只鹰。这些车把无数残缺的肢体和破碎的灵魂从前线拉回来,见证了太多的血和泪。一名从前线回来的司机说他开的那辆车地板缝里渗进去的血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天一热整个车厢里都是一股血腥味。就连那个给阿德勒带来巨大利润的7型打字机也成了战争的一部分。无数的阵亡通知书,就是用它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出来的。冰冷的铅字敲在薄薄的纸上决定了千里之外一个个家庭的毁灭。战争打了四年。四年足以把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变成一个眼神空洞的废人,也足以把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帝国榨干最后一滴血。1918年,战争结束,德国战败。失败的消息传来,阿德勒的工厂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那些日夜不停的机器终于停了下来,工人们走出车间脸上只有茫然,他们输掉了一切。灾难才真正开始,《凡尔赛条约》就像一根绞索套在了德国工业的脖子上,而且越勒越紧。阿德勒被禁止生产任何可能与军事有关的东西。更要命的是作为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工厂里那些最先进的机床设备被法国和比利时的官员贴上了封条,像战利品一样一件件拆走。这比抢劫还要恶毒,他们不仅拿走你的钱,还要打断你的手,让你永远只能乞讨。紧接着,是堪称人类经济史上最荒诞的一幕——魏玛共和国的超级通货膨胀。钱,已经不再是钱,是一堆废纸。阿德勒的财务报表也成了笑话。一辆汽车的标价后面跟着一长串毫无意义的“0”,工人的工资要用麻袋来装。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还买车?阿德勒的仓库里堆满了已经造出来却卖不掉的汽车。那些曾经象征着荣耀和品质的机器现在静静地停在黑暗里,像一座座无人凭吊的墓碑。海因里希·克莱尔,这个一手缔造汽车帝国的老人,在战争期间将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给了儿子,自己退居到幕后。他亲眼看着自己毕生的心血被战争改造成杀人机器,又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这个打击比任何商业上的失败都更致命。1920年,在法兰克福的家中,82岁的海因里希·克莱尔去世了,死得悄无声息。他的葬礼远没有当年发布新车时那般风光。一个时代的巨人就这样倒下了。他死后,留给儿子们和阿德勒公司的不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帝国,而是一个烂摊子。一个被战争掏空,被条约限制,被通货膨胀扼住咽喉的烂摊子。法兰克福上空,那只鹰还在,但它已经重伤,羽毛凌乱,眼神里充满了疲惫和困惑,趴在废墟上舔舐着伤口。它不知道在地平线的另一端,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那场风暴,会带来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下士,会带来一个叫“大众”的竞争对手,也会带来另一次更加彻底的毁灭。一战把阿德勒的翅膀撅折了,凡尔赛条约又往伤口上撒把盐,整个20年代初,这只鹰就趴在地上靠变卖祖上那点家当过活。你猜它靠什么撑着没死?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和打字机。在那个一个面包要卖好几万亿马克的操蛋年代,汽车是国王的梦,但自行车却是邮差的腿,打字机是政府那帮饭桶官僚的嘴。阿德勒就是靠着这两样便宜货,像个得了肺痨的病人一样苟延残喘。海因里希·克莱尔的儿子们,埃尔文和奥托接过这个烂摊子。他们没有老爹那种敢把亲儿子送上赛道的狠劲儿,但他们有德国人那种近乎愚蠢的执拗。他们就一个念头:阿德勒不能死!接着奇迹发生了,或者说一个更大的骗局开始了。美国人,那帮发了战争财的暴发户,开始往德国撒钱。道威斯计划,听着像个慈善项目,其实就是华尔街的放贷员觉得德国这个破产的哥们还有点利用价值,借给他点钱让他先把日子过起来,以后再连本带利地收回来。德国,尤其是柏林,突然就“金光闪闪”了。这就是所谓的“黄金二十年代”。大街上到处都是爵士乐、大腿舞和廉价香槟的味道。人们像疯了一样,在昨天的废墟上开起了今天的派对,假装明天不会到来。阿德勒的管理层也闻到了股骚味。他们觉得机会来了,德国人又有钱了(虽然是借的)需要重新找回尊严。怎么找?于是,阿德勒决定干一票大的,要造一辆能和奔驰、霍希(Horch)掰手腕的豪华车。这就是“Standard 6”(标准六缸)和后来的“Standard 8”。这车,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老子又回来了”的劲儿。发动机平顺得像丝绸,底盘稳得像磐石。但光有这些还不够,他们还要做一件让所有人都闭嘴的事。他们找到了一个人,一个在当时德国比任何一个电影明星都牛逼的人物——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这哥们是谁?包豪斯(Bauhaus)的创始人,现代设计教父。他的那帮信徒天天喊着“形式追随功能”,“拒绝一切不必要的装饰”。他们设计的椅子坐着硌屁股,但看着很高级。他们设计的房子,方方正正像个水泥盒子,但就是能上艺术杂志封面。阿德勒请格罗皮乌斯来设计“Standard 6”的车身。这在当时就相当于苹果公司请了毕加索来设计iPhone 18。所有人都觉得阿德勒疯了,一个搞建筑的,懂什么叫汽车的曲线和激情?格罗皮乌斯交出了作品。那辆车,没有任何多余的线条,平滑、简洁,比例精准得像用圆规和三角尺画出来的。它没有奔驰的霸气,没有意大利车的风骚,就像一座可以移动的、冷冰冰的、充满理性光辉的建筑。它很美,那是一种让人产生距离感的美,一种让你想把它放进博物馆而不是开出去泡妞的美。这辆车成了艺术评论家和建筑师们的最爱,他们写了无数文章来吹捧它的“理性之光”和“工业美学”。但售卖结果呢?一败涂地!一个普通的德国中产,谁特么在乎你是什么狗屁包豪斯,他想要的只是一辆看起来有面子就行的车。格罗皮乌斯设计的这玩意儿,太像个“艺术品”了,太贵,也太“冷”。阿德勒这记大招,就像放了个屁,响声很大却什么也没有。1929年10月24日,纽约华尔街的股票交易机,开始像疯了一样往外吐纸带。大萧条从美国那边刮了过来,到了德国就变成了十二级的飓风。美国人一分钱都不借了,还要把之前的钱要回去。德国的经济,这栋靠着美国贷款搭起来的积木房子,瞬间崩塌。几百万人失业,工厂成片倒闭。阿德勒那高贵的“Standard 6”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就像看着一个穿着晚礼服去要饭的贵族,可笑又可悲。阿德勒又一次被逼到了悬崖边缘,而这一次连退路都没有了。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只鹰死定的时候,它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它没有继续在豪华车市场死磕,而是干脆利落地转身,面向了那些在街上游荡的,口袋里没几个钱的失业者。阿德勒的工程师们在一间满是灰尘的仓库里,翻出了一个被人遗忘却激进得近乎疯狂的设计——前轮驱动(Front-Wheel Drive)。这玩意儿在当时就是个异端。所有“正经”车都是后轮驱动。前面发动机通过一根又粗又长的传动轴把动力传到后面。而前驱是把发动机、变速箱、驱动轮全挤在车头。这能省掉那根传动轴,让车身更轻,底盘更低,车内地板是平的,空间更大。最关键的是它能让造车成本低一大截。但它的技术难题也像个噩梦:转向和驱动搅在一起很容易出问题。也有很多大厂研究过但最后都放弃了。觉得这玩意儿不可靠就是旁门左道。但阿德勒却像一个输光钱的赌徒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这张叫“前驱”的牌上。1932年,一款小车在柏林车展亮相。它没有“Standard 6”那种优雅的身段,甚至有点其貌不扬。但当解说员宣布它采用了“前轮驱动”时整个展厅都蒙了。这款车被命名为“Trumpf”。“Trumpf”,德语里是“王牌”的意思。而且这张牌打对了!紧接着1934年,他们又推出了更小,更便宜的版本——“Trumpf Junior”(王牌少年)。这辆车简直就是为大萧条量身定做的。它不快也不豪华,但它只要2650马克。省油,可靠(阿德勒的工程师们解决了那些技术难题),空间还大。一个失业后重新找到工作的医生可以买一辆去出诊;一个小店主可以开着它去进货。它不是件奢侈品,而是一个在苦难生活中能让你继续前行的工具。“Trumpf Junior”卖疯了。在那个哀鸿遍野的年代,阿德勒的工厂居然开始三班倒了。这辆小车像一支强心针直接扎进了阿德勒那颗快要停跳的心脏里。这只鹰靠着自断一臂的勇气,靠着拥抱异端的技术,居然从悬崖边上又飞了回来。甚至还有余力把“Trumpf”赛车派去参加勒芒24小时耐力赛,并且在同级别里拿下了冠军。法兰克福上空那只鹰的影子重新变得清晰。它瘦骨嶙峋,但眼神锐利。然而,就在阿德勒的工程师们庆祝胜利,工人们为赚到加班费而欢呼的时候。没人注意到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那个最大的赌徒已经上桌了。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奥地利人,正在向全德国人民许诺一个更大的“王牌”——一辆属于全体人民的汽车(Volkswagen),一个强大的第三帝国。阿德勒靠“王牌”活了下来。但很快它就要面对一个把整个国家都当成赌注的疯子。新的,更黑暗的命运,正在前方等着它。这一次就没那么好运了。那个疯狂的赌徒,那个奥地利下士正在兑现他的诺言。他不仅给了德国人工作(虽然是在军工厂),还给了他们一条条像灰色长龙一样盘踞在德国大地上的高速公路。阿德勒的管理层一开始还挺高兴。路修好了,我们的车不就能卖得更好了吗?他们甚至专门设计了一款叫“Adler 2.5 Liter Autobahn”的轿车,流线型的车身能轻松地跑到150公里/小时。这车就是为高速公路而生的,它像一只姿态优美的鹰在这崭新的“天路”上滑翔,展示着阿德勒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优雅。为什么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搞错了一件事。希特勒修路从来就不是为了让你周末开着车载着老婆孩子去郊游的。是为了让他的虎式坦克能在一夜之间从德国东边跑到西边。这路是战争的血管。而他许诺给人民的那辆“大众汽车”(Volkswagen)更是悬在所有德国汽车厂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特么根本就不是一个商业项目,而是一个政治阴谋。费迪南德·保时捷(Ferdinand Porsche)揣摩透了元首的心思,设计出了那台后来风靡全球的甲壳虫。元首的目标很明确:造一辆能让所有德国人都买得起的车,另外还要把“汽车”这个概念从阿德勒、欧宝这些私人公司的手里彻底抢过来变成国家的恩赐,变成纳粹党的福利。怎么抢?很简单!国家控制钢铁,控制橡胶,控制所有战略物资。你想造“王牌少年”?可以,得先排队。等军队订单完成了,等保时捷的“大众”工厂拿到了足够的资源,剩下的那点残羹冷炙才是你们的。阿德勒的工程师们,那些曾经解决了前驱难题的天才,现在每天都在为了一吨钢板、一百条轮胎的配额跟官僚们吵得面红耳赤。他们虽然有全世界最牛逼的设计,但没有材料。那辆漂亮的“Autobahn”轿车成了绝唱。它证明了阿德勒有能力造出世界顶级的汽车,但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它了。1939年9月1日。德军的坦克碾过波兰边境,那条为战争修建的高速公路,终于派上了用场。阿德勒的工厂,再一次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拽到了战争的轨道上。历史这个最爱讲冷笑话的婊子又重复讲了一遍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彻底,更不留情面。工厂的大门上鹰标还在,但下面挂上了第三帝国的万字旗。生产“王牌少年”的生产线开始生产军用车辆的底盘和发动机。那些曾经为勒芒冠军而欢呼的工人们现在沉默地组装着一个个半履带摩托车(Sd.Kfz. 2,又称Kettenkrad)的变速箱(这玩意儿前面是摩托,后面是坦克履带,能把德军士兵带到苏联那泥泞的地狱里去)。打字机车间依旧是最高效的部门。只不过,它敲出来的除了阵亡通知书还有盖世太保的逮捕令加上送犹太人去集中营的名单。那清脆的“咔哒”声,每次敲击都是在为这个帝国的罪恶签下一个名字。整个法兰克福成了战争机器的心脏。白天,工厂的烟囱冒着黑烟;晚上,为了躲避空袭全城都要实行灯火管制,一片死寂,只有巡逻队的皮靴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响。但是报应还是来了。从1943年开始,英国和美国的轰炸机开始像一群愤怒的铁鸟成群结队地飞临德国上空。它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德国的工业心脏,让这台战争机器停下来。1944年3月22日,法兰克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那晚的空袭警报像鬼哭一样响彻全城。几分钟后,地平线就变成了红色。成百上千架兰彻斯特轰炸机打开弹舱,落下来成千上万的高爆炸弹和燃烧弹。阿德勒的厂区是第一波被击中的目标。一枚重磅炸弹直接命中了当年海因里希·克莱尔起家的那个主厂房。爆炸的瞬间,时间好像都凝固了。之后是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砖石、钢梁、玻璃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撕碎,抛向空中。当年伦普勒设计出“一体化动力单元”的那个车间瞬间变成燃烧的地狱。紧接着,燃烧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黏在屋顶上,黏在机器上,黏在那些还没来得及出厂的车辆上,燃起无法扑灭的白磷火焰。整个工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炬,而那只黑色的鹰标在烈焰中卷曲、变形,最后被烧成了焦黑的铁水。一个幸存的老工人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躲在地下防空洞里,能感觉到整个大地像筛子一样抖动,头顶上传来钢筋混凝土断裂时令人牙酸的声音。等轰炸结束他们爬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傻了,工厂没了。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还在冒着黑烟的废墟。那些他们曾经无比熟悉的厂房、仓库、办公楼瞬间全都变成了一堆堆瓦砾。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橡胶、金属和……人肉的味道。海因里希·克莱尔用一生建造的帝国,埃尔文和奥托用半生守护的家业,那只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中都顽强活下来的鹰。在一夜之间,被烧成了灰。1945年5月,战争结束。美军吉普车开进了法兰克福的废墟。几个美国兵跳下车好奇地看着阿德勒工厂的残骸。一个士兵从瓦砾堆里踢出来一个被烧得变了形的但还能依稀辨认出“Adler”字样的金属片。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曾经的故事,只是觉得好玩,又一脚把它踢开了。那只鹰死了。巢穴被夷为平地。一切归零了。1945年,战争结束了,一场持续了六年的高烧,终于退了。而此时,阿德勒的废墟上长满了杂草。克莱尔家族的后人和那些幸存下来的工程师、工人们,站在瓦砾堆前,面面相觑。怎么办?重建?拿什么建?马克已经成了废纸。设备都被炸的稀烂。市场?德国人连裤子都快穿不上了,谁他妈还买汽车?最要命的是,心气儿没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借着马歇尔计划那点可怜的援助,咬碎牙重新拉起汽车生产线。去跟那个在沃尔夫斯堡由英国人扶持的已经开始疯狂下蛋的“甲壳虫”死磕。去跟斯图加特那颗正在从灰烬中重新闪耀的三叉星(奔驰)争夺高端市场。然而,这条路是九死一生。第二条,是彻底忘了汽车,忘了赛道,忘了“亨利亲王杯”和勒芒的荣耀。退回到自己最熟悉,最安全的角落。阿德勒,选择了第二条。这是一个商业上无比正确但在情感上等于公开宣布“老子认怂了”的决定。他们放弃了汽车,这个让他们飞上云端也让他们跌入地狱的梦想。他们开始清理废墟,在还能用的地基上搭起简陋的厂房,重新生产自行车和打字机。阿德勒,又一次靠着起家的这两样玩意儿活了下来。但这一次,性质却完全变了。战后的德国,进入了所谓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时代。整个国家就像一个被彻底格式化后重装系统的硬盘在疯狂地读写。需要记录,需要合同,需要文件,需要把所有的混乱都重新归入秩序。此时,阿德勒的打字机便成了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脚。它不再是那个敲出死亡通知书的冰冷机器。它成了公司前台,政府办公室,银行柜台上的标配。它精准、可靠、耐用,每天,有无数根手指在它的键盘上跳动,敲出来的是一笔笔订单,一份份报告,一个个家庭的新希望。阿德勒的打字机成了德国重建的螺丝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们甚至还给一款便携打字机起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名字——“Gabriele”(加布里埃尔)。当然,他们也曾有过最后一次制造车的挣扎。50年代,他们推出几款非常牛逼的摩托车,比如M250。那台双缸二冲程发动机,设计精巧,性能卓越在赛道上拿奖拿到手软,一度让世人觉得那只鹰的战斗精神还在,但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因为那个叫“甲壳虫”的小怪物已经彻底占领了德国的整个街道。当一个家庭只要花不多的钱就能买到一个能遮风挡雨的铁壳子时,谁还会去买一辆摩托车?摩托的黄金时代,被廉价汽车的到来无情地给终结了。阿德勒的那最后一点野性也被市场规律给阉割了。从此,这只鹰彻底收起了爪牙,不再仰望天空而是低头专注于办公桌上那一亩三分地。1957年,阿德勒与德国另一家办公设备和摩托车制造商“Triumph”(没错,德国也有个凯旋)合并,组成了“Triumph-Adler AG”。之后,它便像个漂亮寡妇,开始了被各路资本轮番倒手的命运。先是被德国电子巨头根德(Grundig)收购,后来,又被大众汽车(Volkswagen)收购。那个当年用政治手段间接扼杀了阿德勒汽车梦的对手,最终像收藏家一样把阿德勒的尸体拖回来放进了自己的仓库。大众要的不是阿德勒的品牌,而是它在办公设备领域那点残存的渠道和技术。再后来,大众又把它卖给了意大利的打字机巨头奥利维蒂(Olivetti)。这简直比让一个法国厨子来定义德国香肠的标准,还要让人哭笑不得。今天,你依然可以在某些地方,找到“Adler”或者“TA Adler”这个牌子的办公设备,复印机、打印机、碎纸机……它们安静、高效地工作着。但那只鹰却已经死了!